家家乞巧望秋月
——咏七夕节古诗词赏析(二)
王传学
到唐时,乞巧习俗更为盛行。盛唐墨客崔颢在《七夕》诗中写道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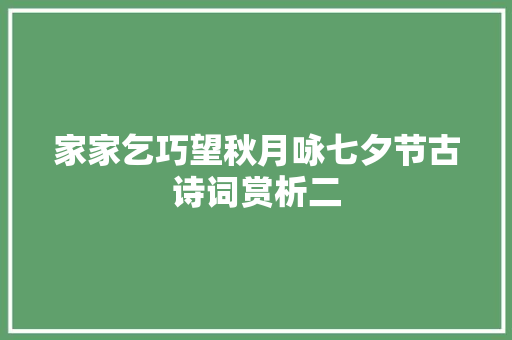
长安城中月如练,
家家此夜持针线。
仙裙玉佩空自知,
天上人间不相见。
长信深阴夜转幽,
瑶阶金阁数萤流。
班姬此夕愁无限,
天河三更看斗牛。
此诗写七夕之夜,皎洁的月光如白练飘落在长安城中,由于喜好牛郎织女,长安城里家家户户的女子都在月下兴趣勃勃地比赛穿针引线。可远在天空中的织女哪里知道人间的这些情形呢,毕竟,天上人间是无法相见的。不过,人们一贯都相信到了七夕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,织女会在天宫的庭阶上等待着和牛郎相会的时候到来,只是迫切想见牛郎的心情以为等待的韶光特殊漫长。织女只好数着面前飞舞的流萤消磨光阴,三更一到,便与心爱的人儿相见。
“长安城中月如练,家家此夜持针线”,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都城长安七夕节穿针乞巧风尚的遍及。
少年墨客林杰的《乞巧》诗,被公认为唐代描写七夕“乞巧”的代表作:
七夕今宵看碧霄,
牵牛织女渡河桥。
家家乞巧望秋月,
穿尽红丝几万条。
林杰(公元831—847年)字智周,唐代墨客。小时候非常聪明,六岁就能赋诗,下笔即成章。又精书法棋艺。年仅十七岁。《全唐诗》存其诗两首。
《乞巧》是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。农历七月初七夜晚,俗称“七夕”,又称“女儿节”“少女节”。是传说中隔着“天河”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的日子。过去,七夕的民间活动紧张是乞巧,所谓乞巧,便是向织女乞求一双巧手的意思。乞巧最普遍的办法是对月穿针,如果线从针孔穿过,就叫得巧。这一习俗唐宋最盛。
“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”,“碧霄”指浩瀚无际的上苍。开头两句阐述的便是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。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,家家户户的人们纷纭情不自禁地举头仰望浩瀚的天空,这是由于这一俏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,唤起人们美好的欲望和丰富的想象。“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”,后两句将乞巧的事交代得一目了然,简明扼要、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人们过七夕节时乞巧祈福的心情。墨客在诗中并没有详细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,而是留下想象的空间,展示了人们乞取智巧、追求幸福的心愿。
唐代墨客祖咏的《七夕》诗,描述了乞巧穿针的难度:
闺女求天女,更阑意未阑。
玉庭开粉席,罗袖捧金盘。
向月穿针易,临风整线难。
不知谁得巧,明旦试寻看。
祖咏(公元699—约746年),盛唐墨客。诗多状景咏物,鼓吹隐逸生活。其诗讲求对仗,亦带有诗中有画之色彩,与王维友善,以《终南望余雪》和《望蓟门》两首诗最为著名。有诗一卷。
墨客的女儿七夕向天女乞巧,夜深了依然兴趣盎然。庭院中摆着供席,双手捧着金盘。对月穿针,最难的是临风理线。以是谁能乞到巧,只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知晓。
再看五代墨客和凝的《宫词百首》之五十五首:
阑珊星斗缀珠光,
七夕宫嫔乞巧忙。
总上穿针楼上去,
竞看银汉洒琼浆。
和凝(公元898—955年),五代期间文学家、法医学家。好文学,长于短歌艳曲。后唐时官至中书舍人,工部侍郎。后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入后汉,封鲁国公。后周时,赠侍中。尝取古今史传所讼断狱、辨雪冤枉等事,著为《疑狱集》四卷。
此诗写七夕当晚,天空中稀疏的星斗像缀着的宝珠闪闪发光,皇宫中的妃嫔们忙着向织女乞巧。大家都登上穿针楼,争着看天上的星星发出的闪亮银光。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宫中女子登楼乞巧的情景。
乞巧风尚至宋代最盛。据宋代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记载:“七夕前三五日,车马盈市,罗绮满街,……至初六日、七日晚,贵家多结彩楼于庭,谓之‘乞巧楼’。铺陈磨喝乐、花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,或儿童裁诗,女郎呈巧,焚喷鼻香列拜,谓之‘乞巧’。妇女望月穿针。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,越日看之,若网圆正,谓之‘得巧’。”这些描述展现了北宋七夕节之盛况。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卷四云:“七月七日,谓之‘七夕节’。其日晚晡时,倾城儿童女子,不论贫富,皆着新衣。富贵之家,于高楼危榭,安排筵会,以赏节序,又于广庭中设喷鼻香案及酒果,遂令女郎望月,次乞巧于女、牛。”生动描述了南宋七夕节的乞巧风尚。
宋代七夕诗词首先将目光投注于七夕节的民俗活动,展现了乞巧的场景和情态。
宋代词人柳永《二郎神》中有“运巧思,穿针楼上女,抬粉面、云鬟相亚”的描写,词中表现了民间的七夕乞巧活动,将女子对月穿针、乞求巧手的持重与虔诚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了。
宋代墨客钱惟演的《戊申年七夕》,描述了乞巧楼的精美壮不雅观:
骊阜凌云对玉钩,
千门高切绛河秋。
欲闻天语犹嫌远,
更结三层乞巧楼。
钱惟演(公元977—1034年)字希圣。北宋大臣,西昆体骨干墨客。官至工部尚书,拜枢密使。博学能文,所著今存《家王故事》、《金坡遗事》。
宋代有搭建乞巧楼来乞巧的风尚。诗中描述了乞巧楼的高大雄伟,构造的风雅豪华,突出了人们对七夕乞巧的重视。
南宋词人张孝祥的《二郎神•七夕》下片,描写了南宋都邑七夕的盛况:
南国。都会繁盛,依然似昔。聚翠羽明珠三市满,楼不雅观涌、参差金碧。乞巧处、家家追乐事,争要做、丰年七夕。愿明年强健,百姓欢娱,还如今日。
张孝祥(公元1132-1169年)字安国,号于湖居士。南宋词人。官至中书舍人。坚持抗战主见,遭主和派打击,几番起落,究竟没能实现自己的政管理想。作为南宋初期著名文人,其文体靡所不该,而忧国慨敌的情怀无所不在。其文不如诗,而诗则不如词。其词“豪壮典丽”,尤以忠愤悲慨的爱国词为世所名。著有《于湖集》40卷、《于湖词》1卷。
七夕节,南首都会,琳琅满目的华美事物,家家户户的乞巧宴赏,百姓非常欢娱。词人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安乐的七夕节日图。
对七夕乞巧的狂热,有些墨客是持否定态度的。如北宋墨客杨朴的《七夕》诗:
未会牵牛意如何,
须邀织女织金梭。
年年乞与人间巧,
不道人间巧已多。
杨朴(公元921—1003年)字契元,自号东里野民,北宋布衣墨客。好学,善诗,天性恬淡孤僻,不愿做官,终生隐居屯子。常独自骑牛游赏,往来于县境东里、郭店间。当时的士人学子多传阅诵读他的诗文。其诗俊逸洒脱,措辞朴实精髓精辟,多描写自然景致和屯子隐居生活。类唐墨客贾岛、李涉。著有《东里集》。
这首诗大意是说:不明白牵牛的用意是怎么回事,每年七月总要约请织女在天上穿梭织锦给地上的人们看。你们年年让人间乞得巧去,岂不知道人间的巧多得很哩!
说不知道牛郎想怎么样,难道应教织女传技巧?年年给予人间技巧,不知人间机巧已多得恐怖!
全诗对乞巧、给巧的行为予以否定,讥人间“机巧”泛滥,使诗的情思、哲理向更深层次开掘,使小诗具有横空出世、奇崛诡辩的美学代价。
南宋词人吴潜的《鹊桥仙》,对七夕乞巧进行嘲笑:
馨喷鼻香饼饵,新鲜瓜果,乞巧千门万户。到头人事控抟难,与拙底、无多来去。
痴儿企图,夜看银汉,要待云车飞度。谁知牛女已尊年,又那得、欢娱意绪。
吴潜(公元1195—1262年) 字毅夫,号履斋。南宋词人。官至尚书金部员外郎。其词多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与报国无门的悲愤。格调沉郁,感慨特深。著有《履斋遗集》,词集有《履斋诗余》。
七夕节,家家户户在庭院摆上供桌,上面陈放着精美食品和新鲜瓜果,向织女乞巧。有的痴痴地等待,想看到云车在天河上飞渡。词人嘲笑道:牛郎织女年事已高 ,那里还有什么欢娱意思呢!
宋后历朝沿袭唐宋旧俗,据明人刘侗、于奕正同撰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,乞巧形式不断出新,花样愈来愈多。除穿针乞巧、卜巧外,更盛行“丢巧针”的游戏。方法是在七月七日这天上午,拿一盆水曝晒日中,待水面凝成薄薄的一层膜后,此时把平日缝衣或绣花的针投入盆中,针便会浮在水面上。丢针的妇女便心神专注地看水底的针影,如果成云物花朵之影,或细直如针形者,便是“乞得巧”,由于这些影子表示织女赏给她一根机动的绣花针,可以织绣出俏丽的图案;如果水底针影粗如槌,或波折不成形者,就表示丢针的妇女是个“拙妇”,由于织女给她的是一根石杵。“针能浮水”这个有趣而不可思议的活动,在明人刘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,清人顾禄的《清嘉录》、让廉的《春明岁时琐记》等书里,都有较详尽的记载。
元代散曲家杜仁杰的《【商调】集贤宾北•七夕》,写出了元代官宦家女子乞巧的过程(选个中三支曲子):
【集贤宾南】今宵两星相会期,正乞巧投契。沉李浮瓜肴馔美,把几个摩诃罗儿摆
起。齐拜礼,真个是塑得来可嬉。
【凤鸾吟北】月色辉,夜将阑银汉低,斗穿针逞艳质。喜蛛儿奇,一丝丝往下垂,结罗成巧样势。酒斟着绿蚁,喷鼻香焚着麝脐,引杯觞大家沉醉。樱桃妒水底红,葱指剖冰瓜脆,更胜似爱月夜眠迟。
【节节高北】玉葱纤细,粉腮娇腻。争妍斗巧,笑声举,欢天喜地。我则见管弦齐
动,商音夷则。遥天外斗渐移,喜阴晴今宵七夕。
杜仁杰(约公元1201—1282年),原名之元,别号征,字仲梁,号善夫。元代散曲家。《录鬼簿》把他列入“前辈已去世名公。”他由金入元,元初屡被征召不出。性善谑,才学宏博。其著作有《逃空丝竹集》、《河洛遗稿》,惜皆早佚。现存诗作二十八首,词二首,散曲六首。
散曲写七夕节到,人们在庭院中供上精美的瓜果佳肴美馔,妇女们精心打扮,争妍斗巧;喷鼻香焚麝脐,酒斟绿蚁,管弦齐动,向织女星乞巧。
清代女墨客徐瑛玉《乞巧》诗,则以其女性所独具的细心和谅解来看乞巧,也别有新意:
银汉横斜玉漏催,
穿针瓜果置妆台。
一宵要话经年别,
那得工夫送巧来?
徐瑛玉(生卒年不详),清代学者沈大成的女弟子,字若冰,嫁孔氏,能诗,早亡。其和沈大成《送春》云:“春光苦处两蹉跎,愁见飞花槛外过。漫说穷愁诗便好,算来诗不敌愁多。”时人称许。
诗中写道:七夕这天,女人们早早地就把针线和瓜果摆在装扮台上。只见银河横流,光阴飞逝,可牛郎织女要在短短的一夜韶光里诉说积攒了一年的知心话,那里还有工夫送巧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