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单说它令人谈之色变,或许很多人没有观点,不知道这种传染病的胆怯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到《中华公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,在个中,规定了传染病分为三个等级,甲类、乙类和丙类。
甲类传染病(暴发、盛行情形和危害程度最高的传染病)是指:鼠疫、霍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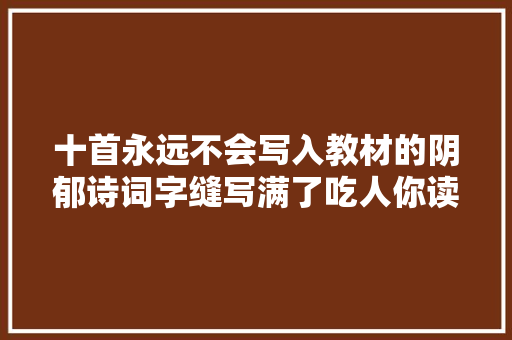
而2003年爆发的非典,以及离我们不远,曾导致全国一度数次封城隔离的新冠,都只是被列为乙类传染病。
这样,该当就不丢脸出鼠疫的胆怯了吧。
对付我们大多数人来说,这种传染病可谓是相称迢遥,险些都已经忘却了它的胆怯毁坏力。作为历史上为祸剧烈的传染病,鼠疫的魔影曾一度笼罩全体欧洲大陆数百年,挥之不去。造成了上千万人去世亡,改写了全体欧洲的发展进程。
不独是欧洲,中国也曾经爆发过鼠疫,而上面这首《去世鼠行》写得正是鼠疫爆发的胆怯场景。
师道南,清朝中叶,云南大理白族的著名墨客,彼时,全体云南正逢鼠疫肆虐,师道南身处个中,用笔墨详细地记录下了这宛若人间炼狱的胆怯场景。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胆怯场景呢?
“东去世鼠,西去世鼠,人见去世鼠如见虎!
鼠去世不几日,人去世如圻堵”,先是老鼠不断地去世亡,无比渗人,紧接着,人也开始大规模地传染,相继去世去。
“昼去世人,莫问数,日色惨淡愁云护。三人行未十步多,忽去世两人横截路。夜去世人,不敢哭,疫鬼吐气灯摇绿。须臾风起灯忽无,人鬼尸棺暗同屋。”
白天黑夜,人去世无数,有时候,三个看似正常的人在路上行走着,溘然之间,就有两个去世在路上。全体疫区,各处去世人,活人与尸体,棺椁同屋,去世气萦绕,鬼影憧憧,宛若地狱。
“白日逢人多是鬼,薄暮遇鬼反疑人!
人去世满地人烟倒,人骨渐被风吹老”,去世人见多了,白日里看到那些敢出来的人,反而疑惑他们是鬼,不然,怎么会不怕这些瘟疫呢?到了晚上,就算是见到鬼,也反而认为他们是人,大抵是此间的人熏染去世气,饱受鼠疫折磨,又看着无数亲朋好友去世去,早已经变得面色胆怯,见惯了去世人和面色胆怯的人,见到鬼了,也就以为再正常不过,和人没什么两样。
“我欲骑天龙,上天府,呼天公,乞天母,洒天浆,散天乳,酥透九原千丈土。地下大家都活归,黄泉化作回春雨!
”
看到这样的人间惨剧,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御龙飞升,到达天庭,向天帝王母乞求来玉露琼浆,洒向人间,浸润这片地皮,驱散瘟疫,让地下去世去的人,大家都能够复活。
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,再加上人们对付鼠疫的理解不敷,根本无法有效地阻挡疫情的扩散,鼠疫猖獗肆虐,无数人去世去,城市村落落变得荒无人烟。
就连这首诗的作者师道南也同样没有熬过去,去世在了鼠疫中!
《秦妇吟》,晚唐墨客韦庄笔下一部鸿篇巨制的史诗,全文有1666字,238句,比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多了将近一倍,诗中借助秦妇的口吻,写出了黄巢农人军攻占长安后的社会状况,社会衰败,民生凋敝。
这首长诗,写出社会现实的深刻,无论是辞藻还是境界,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,后人赞誉如潮,它与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木兰辞》并称为“乐府三绝”,就连韦庄,也因此被称为“秦妇吟秀才”。
唐朝末年,大唐天子早就已经没有能力掌控弘大的帝国,也在一次次地方藩镇的武力威胁下,失落去了中枢的肃静,“首都六陷,天子九逃”,君不君,臣不臣,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秦妇吟,不仅戳穿了黄巢义军的野蛮横暴,也展现了官军的滔天恶行,个中各类,让人读之泪下,或许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原由,《秦妇吟》神秘地失落传了,直到千年后的1900年,人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,才找到了其刻本,让这首长诗重见天日。
唐朝期间,南方经由历代的开拓,已经变得相称繁华,又兼之地皮肥沃,景象适宜,可谓是富饶无比,更是有着“扬一益二”的说法。
而关中经历过安史之乱,几十万的大军厮杀,全体中原和关中平原都被打的稀巴烂,残破无比,江南的富饶也就愈发明显。
可偏偏这样的富庶之地,竟然涌现了“是岁江南旱,衢州人食人”的场景,如果真的是碰着百年难遇的旱灾,人吃人的场景固然让人不忍看,但天灾无情,也没有办法。可这偏偏是人祸。
这样的灾害是什么人造成的呢?
白居易没有直言,但他用极长的篇幅刻画了那些宦官骄奢淫逸的生活。
这些宦官们,朱绂紫绶,吃着山珍海味,喝着美酒佳酿,水果是洞庭湖的优质品,心满意足地吃着这些难得的珍品,神气骄横无比。
也正是如此,才愈发讽刺,百姓人食人的人间惨剧下,是那些宦官借着皇权,四处游走,享受供奉。
诗圣杜甫笔下的笔墨,是他所经历的人生,也是大唐那个期间的真实表示,他的一些诗句堪比正史,乃至有未被正史收录进的历史,以是被称为“诗史”。一些诗句因太过“史实”而难以广泛传播。正如这首三绝句。
《三绝句》虽真实,但也因真实而过于残酷。诗文大略,很多人不用翻译也能读懂,但也正是如此,很多人不愿意翻译,也不想读懂它,缘故原由无他,血淋淋的现实太过残酷,读完之后,让人以为心头沉甸甸的,很压抑,一点都不舒畅。
这里用我自己的理解翻译一下:前年渝州刺史被杀,今年开州刺史被杀。群盗蜂起比虎狼还厉害,他们吃起人来更乐意留下妇孺吗?二十一户家人结伴去蜀地逃难,末了只剩一人走出了骆谷。这一人提及自己的两个女儿咬臂起誓一定要走出骆谷时,回望他走来的秦岭的天空,哽咽不能语。禁军虽然骁勇雄壮,论起施暴来却与羌人、土浑人相同。听说他们在汉水边上杀人,而妇女们多被掳掠胁迫至军中。
“二十一家同入蜀,惟残一人出骆谷”,唐朝时的一户人家和现在不同,现在一户人不过一家两代人,唐时,是三四代人一起,称为一家,以是二十一家结随同行,人数绝对不少。可便是这些人,一起逃入蜀地寻求活路,却只有一个人走出骆谷。其他人去哪里了?不得而知,但联系前文的“食人更肯留妻子”,他们的去向不言而喻!
这些盗寇肆虐一方,难道朝廷就不管吗?
杜甫紧接着给出了答案。
“殿前兵马虽骁雄,纵暴略与羌浑同。闻道杀人汉水上,妇女多在官军中”,这些官军虽然骁勇善战,但论起施暴,他们丝毫不亚于那些凶神恶煞的羌人,土浑人。
“匪过如梳,兵过如篦”,从来不是一句空话,这些官军在汉水边大肆屠戮,抢夺钱财,将妇女全部掳掠到军营中。
“岁大饥,人相食”,“岁饥馑,人相食”,这些话于史籍中习认为常,已成为史籍中的固有范式,且摆脱不掉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,鲁讯《狂人日记》中所写:“我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熟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四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!
”。这里的吃人,也不仅仅是封建礼教吃人,更是字面上的吃人,浊世吃人,习认为常!
这首诗的作者存疑,有说李璟,有说南唐后主李煜,且都有相应的书本记载(前者出自《新编分门古今类事》与《翰苑名谈》,后者出自《增修诗话总龟》和《全唐诗》)。这里就不作考证。
不过,不管这首诗的作者是这父子俩中的何人,这首诗都相称的渗人。
正所谓“诗以言志,歌以咏怀,文以载道”,诗词文章每每是一个人内心天下的展现,从笔墨中不丢脸出作者的意图。
荷花娇艳俏丽,出淤泥而不染,在历代文人笔下,要么是将之比作娇艳的美人面庞,“芙蓉如面柳如眉”,“芙蓉向脸两边开”;要么便是赞颂其亭亭玉立,出淤泥而不染的风采,“惟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”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
可偏偏在这首诗中,荷花绽放,不似其他,反而是像一个个被人砍下来的美人头。千顷俏丽荷花,宛若一个个美人头一样,光是想想,就以为不寒而栗。
每逢浊世,军阀混战,各种野心家从各地冒出来,彼此厮杀混战,此时的百姓最是悲惨。
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中原原来最是繁华富饶,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,可是频年的征战,以至于白骨累累,暴露在荒野外,任由风吹雨打,而这样的千里沃野,竟然毫无人烟,让人如何不泪垂。
如果说,在明末抗清中,哪一座城市最为刺目耀眼,那么毫无疑问,一定是江阴!
面对清军的猖獗压迫,江阴百姓忍无可忍,杀去世清朝派来的知县和驻扎的清军,公推前后两任典史(掌管文书出纳的小官)陈明遇、闫应元领导武装抗清。
八十一天的江阴保卫战,城内城外,无数百姓前赴后继,万去世不屈,哪怕是三尺童子,也都不惧刀芒。纵然去世亡无数,老弱妇孺也都上城墙帮忙守城,没有一个人肯屈膝降服佩服。
万去世孤忠未肯降,炎黄子孙的铮铮骨气仿佛汇聚到了这里。
已是晚年的老者,志愿带着炸药,出城诈降,引爆炸药,纵是自身尸骨无存,也要炸去世清军。
城墙上,妇孺为义军战士搬运石块,箭矢,煮沸的金汁。形势危急时,也能握住手中刀枪,将爬上城墙的仇敌砍去世,若是力有不逮,乃至直接拉着仇敌从城墙上一跃而下,壮烈如此!
一寸山河一寸血,这江阴城上,满是忠魂傲骨!
“寄语行人休掩鼻,活人不及去世人喷鼻香”,如果说其他的诗句是阴郁胆怯,那么,江阴城外,纵然是尸骸遍野,骨暴沙砾,也不会让人以为压抑胆怯,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,他们的铮铮铁骨值得每一个人尊敬。
这座城市永垂不朽,这座城市中所有参与抗清的公民永垂不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