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7月,在《经典咏流传》这期节目上,一位贵州山区的老师梁俊带领他的学生们演唱了《苔》这首古诗,一韶光刷爆了朋友圈,许多人在歌曲下留言\公众泪目\公众。
梁俊在贵州乌蒙山支教了两年,在这两年里,他把古诗编成吉他曲,让乌蒙山里的孩子们和诗以歌,记住了一百多首古诗。有了这些底子后,孩子们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。
梁俊说:\"大众还记得为什么要唱这《苔》吗?\公众
他的学生回答:\"大众由于要让我们像牡丹一样年夜胆地开放。\公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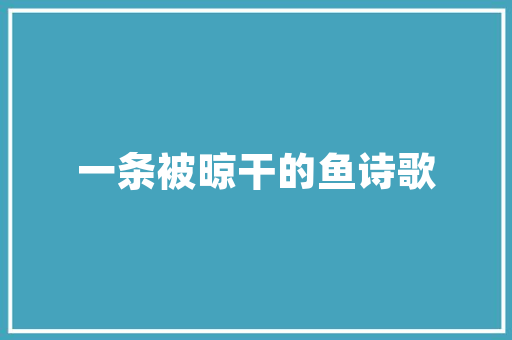
梁俊将自己和学生比喻成苔,生于惨淡幽湿的角落,不为众人所见,却也要开出花来,实现自己生命的代价。
如果我们去看《苔》后的评论,会看到大量高三党的自我勉励之言,它并非很深奥华美的诗歌,相反显得朴素而浅近:
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
这是清代袁枚的诗,袁枚何许人也?性灵说的提倡者。这首小诗措辞流畅,风格活泼轻灵,很有些自然纯洁的意趣。然而熟读文言诗词的高三党人口味早已被养刁,论手腕辞藻,《苔》并非上乘之作,何以得人如此青睐?
2、《苔》在对大众说:\公众我瞥见了你们的美好\"大众
\"大众苔花\公众比喻的是所有默默无闻而努力活出精彩的人。这一人群遍布社会各行各业,深夜攻读的高三党,三线小明星,普通的职场员工、深夜辗转难眠的人等等,\公众泯然众人\"大众的人究竟是大多数,这么一大群拼格斗争的普通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看到了\"大众苔花\"大众的影子。而袁枚以朴素朴拙的措辞去赞颂苍苔,是对芸芸众生行了瞩目礼,\"大众我看到了你们的美好\"大众。
大众渴望自己成为文学的描写工具,希望自己的苦难和美好都能被文学描写下来。同写冤屈,要说屈原的《怀沙》《哀郢》没几人能念下来,但提及《窦娥冤》却大家熟知\"大众地也,你不分好歹作甚地;天也,你错勘贤愚做天。\"大众同是小说,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写的还是绅士贵族的言谈和趣事,明代冯梦龙已经在写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《白玉娘忍苦成夫》这样以小市民为主角,充满俚俗传奇色彩的文章了。
3、《苔》是\"大众平民文学\公众的胜利
《苔》的盛行,意味着普通人的声音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。近期热播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《无名之辈》《大佛普拉斯》,上溯至周星驰系列电影,音乐领域如彩虹合唱团,歌曲《老男孩》,文学领域如莫言的小说和其\"大众作为老百姓写作\公众的平民文学不雅观等,社交媒体领域如快手、抖音的繁荣全方位地反响了各领域平民化的趋势。
文学领域的平民化,古已有之。中国古代官、士、民三分天下,文学的主导权紧张在\"大众官\"大众和\"大众士\"大众的手里,而唐宋代商品经济繁荣,市民阶层兴起,俗文学地位逐渐上升。清末民初,随着口语文运动的兴起,周作人、茅盾等人对\"大众人的文学\公众的倡导,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传播,文学就越来越趋向于关注民众、做事社会。中国自古就以宗族家国为大,以个人生命体验为轻,讲究文以载道。《苔》是反响人生和人性的诗,只关系小小个体的微小与光辉,不讲大道理也无关大集体,这样的文学盛行,意味着个体的觉醒,正是平民文学的胜利。